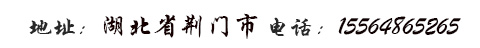赵国华论汉光武帝对乌桓的治理方略
|
彭洋讲白癜风 http://baidianfeng.39.net/a_ht/210722/9216450.html 《秦汉研究》专辑 论汉光武帝对乌桓的治理方略 赵国华 (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) 摘要:汉光武帝对乌桓的治理方略包括三个层次,从军事征伐到金爵笼络,再从金爵笼络到制度管理,其中军事征伐是削弱乌桓的基本手段,金爵笼络是联结乌桓首领的关键因素,制度管理是治理乌桓的终极目标。这一方略的形成和实施,在较短时间内解决了乌桓问题,从而对东汉王朝、乌桓乃至东北亚地区,都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。 关键词:东汉乌桓汉光武帝边疆治理 汉光武帝对乌桓的治理方略,直接关系到东汉王朝北部边疆的安全稳定,也影响到乌桓社会的发展前景,是东汉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。本文拟从边疆治理的角度,叙述和分析汉代乌桓的政治生态,东汉王朝和乌桓的互动关系,揭示光武帝治理乌桓的措施及其实践意义。 一 乌桓,本是东胡的一个分支,西汉初年被匈奴冒顿单于击破,据守在乌桓山(在今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),因以山名为族号。乌桓部族“俗善骑射,随水草放牧,居无常处,以穹庐为宅”[1],还处于早期文明时代。从地理位置来看,乌桓南临汉朝,西接匈奴,北连鲜卑,东望高句丽,具有特殊的地缘关系。这种地缘关系使乌桓与汉朝紧密相连,也与匈奴、鲜卑等部族休戚相关,在一定程度上支配着乌桓的历史命运。 西汉中期,汉武帝对匈奴开展大规模的反击,长期受匈奴奴役的乌桓被迫卷入战争。元狩四年(前年),卫青、霍去病发起漠北之战,分别击破匈奴单于和左贤王,“匈奴远遁,而幕南无王庭”[2],匈奴左部人去地空,汉朝廷“因徙乌桓于上谷、渔阳、右北平、辽西、辽东五郡塞外,为汉侦察匈奴动静。其大人岁一朝见,于是始置护乌桓校尉,秩二千石,拥节监领之,使不得与匈奴交通。”[3]这是汉朝管控乌桓的开端,其中设置护乌桓校尉的目的,主要是保护和监视乌桓,断绝乌桓与匈奴的联系,而乌桓首领统辖其部众,迁徙到汉朝东北五郡塞外,每年要到京城长安朝觐。汉朝廷从制度层面确立了对乌桓的治理模式。 经过汉武帝的持续打击,匈奴的势力受到削弱,而乌桓的力量逐渐壮大。随着匈奴西遁和南迁,乌桓部族不断地西迁,最远到达今鄂尔多斯草原[4]。汉昭帝时期,乌桓族人“发掘匈奴单于冢,将以报冒顿所破之耻”[5],与匈奴处于敌对关系。元凤三年(前78年),匈奴壶衍鞮单于征调骑兵二万人,向东进击乌桓。大将军霍光得到报告,任命中郎将范明友为度辽将军,率领骑兵二万人,从辽东郡出击匈奴。匈奴骑兵劫杀乌桓族人,而后迅速撤退。范明友未能截击匈奴,就趁机进攻乌桓,斩杀乌桓六千多人,俘虏三名乌桓首领[6]。从此以后,乌桓再度侵扰幽州,屡次被范明友击退。直到汉宣帝时期,随着边疆治理的推进,汉朝北部边郡较为安定,乌桓部族转而居边守塞,又降附于汉朝。 到了新朝,为了彻底打垮匈奴政权,王莽大规模地征发兵役。其中,“使东域将严尤领乌桓、丁令兵屯代郡,皆质其妻子于郡县。乌桓不便水土,惧久屯不休,数求谒去。莽不肯遣,遂自亡畔,还为抄盗,而诸郡尽杀其质,由是结怨于莽。”[7]与此相反,匈奴乌累单于见机行事,利诱乌桓首领为属吏,笼络剩余的乌桓族人,使他们归附于匈奴,继续侵扰新朝北部边郡。 从以上史实来看,汉武帝时期击破匈奴左部,把乌桓迁移到东北五郡塞外,设置护乌桓校尉,藉以保护和监视乌桓,使乌桓首领定期朝觐,这是治理乌桓的成功经验。新朝末期,王莽驱使乌桓攻打匈奴,却以杀戮质子与乌桓结怨,乌桓首领反而归附匈奴,这是管控乌桓的失败教训。这些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,给光武帝治理乌桓提供了历史借鉴。 二 新朝灭亡以后,北部边疆陷入混乱状态。乌桓没有建立独立政权,主要依附于匈奴,效命于地方割据势力,经常侵扰北部边郡。光武帝经略河北期间,曾经任命吴汉、耿弇为大将军,“持节北发十郡突骑”[8],参与进攻邯郸之战。所谓“十郡”,指幽州所辖涿郡、渤海、上谷、渔阳、右北平、辽西、辽东、玄菟、乐浪九郡和广阳国;所谓“十郡突骑”,又称“幽州突骑”,指从幽州征发的擅于冲锋陷阵的骑兵部队;这支部队中乌桓族人占有一定的数量,所以亦称乌桓突骑。 建武元年(25年)六月,东汉王朝建立以后,光武帝致力于统一全国,逐个消灭地方割据政权。乌桓与匈奴连结在一起,凭借骑兵作战的优势,经常侵扰东汉王朝北部边郡,给代郡以东地区的民众造成了严重的伤害。《后汉书·乌桓列传》记述: 光武初,乌桓与匈奴连兵为寇,代郡以东尤被其害。居止近塞,朝发穹庐,暮至城郭,五郡民庶,家受其辜,至于郡县损坏,百姓流亡。其在上谷塞外白山者,最为强富。[9] 这里说的白山乌桓,生活在今河北沽源境内,是乌桓部族中一个较强的邑落,主要是侵扰上谷郡。光武帝应对乌桓和匈奴侵扰的措施,是选派一些开国将领担任北部边郡太守,采取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,一面加强北部边郡的军事力量,随时反击匈奴和乌桓的侵扰,一面调动大量的人力和物力,构筑北部边疆的防御系统,维护北部边郡的安全和稳定。其中,王霸、祭肜分别担任上谷、辽东太守,在边疆治理方面留下了显著的政绩。 建武九年(33年),为了消灭卢芳在五原建立的割据政权,光武帝派遣大司马吴汉统领横野大将军王常、建义大将军朱祐、讨虏将军王霸和破奸将军侯进所部5万多人,进攻高柳。因为作战失利,吴汉返回洛阳,指令朱祐驻守常山郡,王常驻守涿郡,侯进驻守渔阳郡。同时光武帝特意下诏,“拜霸上谷太守,领屯兵如故,捕系胡虏,无拘郡界。”[10]此后,王霸一直任职于上谷郡,长期与匈奴和乌桓交战,直到南匈奴和乌桓归附汉朝。《后汉书·王霸传》记述: 是时,卢芳与匈奴、乌桓连兵,寇盗尤数,缘边愁苦。诏霸将弛刑徒六千余人,与杜茂治飞狐道,堆石布土,筑起亭障,自代至平城三百余里。凡与匈奴、乌桓大小数十百战,颇识边事,数上书言宜与匈奴结和亲,又陈委输可从温水漕,以省陆转输之劳,事皆施行。后南单于、乌桓降服,北边无事。[11] 王霸担任上谷太守,从建武九年到永平二年(59年),经历了26年时间。为了抵御匈奴和乌桓的侵扰,光武帝诏令王霸率领弛刑徒六千多人,与骠骑大将军杜茂一道,负责修筑飞狐道。这条通道东起代郡高柳,西到雁门郡平城,延绵三百余里,构筑起一道边塞防御系统。在担任上谷太守期间,王霸与匈奴、乌桓大小数十百战,曾经多次给光武帝上书,建议朝廷与匈奴和亲。这些对光武帝治理乌桓都会有一定的影响。 祭肜是征虏将军祭遵的堂弟,早年被光武帝任命为黄门侍郎,历任偃师县长、襄贲县令。“当是时,匈奴、鲜卑及赤山乌桓连和强盛,数入塞杀略吏人。朝廷以为忧,益增缘边兵,郡有数千人,又遣诸将分屯障塞。帝以肜为能,建武十七年,拜辽东太守。”[12]辽东与上谷、渔阳、右北平、辽西诸郡都是匈奴、乌桓和鲜卑侵扰严重的地区。祭肜担任辽东太守,从建武十七年(41年)到永平十二年(69年),经历了28年时间,在应对匈奴、乌桓和鲜卑侵扰方面,进行了一系列活动。《后汉书·祭遵列传》记述: 建武十七年,拜辽东太守。至则励兵马,广斥候。肜有勇力,能贯三百斤弓。虏每犯塞,常为士卒前锋,数破走之。 肜以三虏连和,卒为边害,二十五年,乃使招呼鲜卑,示以财利。其大都护偏何遣使奉献,愿得归化,肜慰纳赏赐,稍复亲附。其异种满离、高句骊之属,遂骆驿款塞,上貂裘好马,帝辄倍其赏赐。 初,赤山乌桓数犯上谷,为边害,诏书设购赏,切责州郡,不能禁。肜乃率励偏何,遣往讨之。永平元年,偏何击破赤山,斩其魁帅,持首诣肜,塞外震詟。[13] 这里所谓“三虏”,指匈奴、鲜卑及赤山乌桓。赤山乌桓生活在内蒙古赤峰境内,也是乌桓部族中一个较强的邑落。在担任辽东太守期间,祭肜采用征讨和利诱相结合的手段,有效地打击和削弱了赤山乌桓和鲜卑势力,维护了北部边疆的稳定。因此,“肜之威声,畅于北方,西自武威,东尽玄菟及乐浪,胡夷皆来内附,野无风尘。”[14] 然而,乌桓作为一个游牧部族,带有较强的地域流动性,致使汉朝边郡难以管控。即使向南迁徙以后,乌桓部族接受北部边郡的征调,协助进攻匈奴和鲜卑,有时仍会联合匈奴和鲜卑,反过来侵扰北部边郡。所以,直到建武二十年(44年),东汉王朝北部边疆仍处于军事防御状态。这年秋天,伏波将军马援平定交趾徵侧、徵贰,率军返回洛阳。在到达洛阳之前,有许多故人前来迎贺,其中孟冀与马援有一段对话,开启了继续征讨乌桓的进程。《后汉书·马援列传》记述: 援曰:“方今匈奴、乌桓尚扰北边,欲自请击之。男儿要当死于边野,以马革裹尸还葬耳,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!”冀曰:“谅为烈士,当如此矣。”还月余,会匈奴、乌桓寇扶风,援以三辅侵扰,园陵危逼,因请行,许之。自九月至京师,十二月复出屯襄国。……明年秋,援乃将三千骑出高柳,行雁门、代郡、上谷障塞。乌桓候者见汉军至,虏遂散去,援无所得而还。[15] 这里作一点分析,在马援和孟冀看来,要想保住既有的功名,或者成为一位“烈士”,就必须投身于北部边疆,在与匈奴、乌桓征战中建立新功。“男儿要当死于边野,以马革裹尸还葬耳”,这一豪言壮语的迸发,竟然牵连着马援的前途。所以,马援回到洛阳,只过了一个多月,又领兵驻守襄国。建武二十一年(45年)秋天,马援率领骑兵三千人,从高柳出发,连续巡行雁门、代郡、上谷三郡边塞系统。不过,关于这次军事行动,《后汉书·乌桓列传》另有记述: 建武二十一年,遣伏波将军马援将三千骑,出五阮关掩击之。乌桓逆知,悉相率逃走,追斩百级而还。乌桓复尾击援后,援遂晨夜奔归,比入塞,马死者千余匹。[16] 曹魏史学家王沈编纂的《魏书》亦有记述: 光武定天下,遣伏波将军马援将三千骑,从五原关出塞征之,无利,而杀马千余匹。乌桓遂盛,钞击匈奴,匈奴转徙千里,漠南地空。[17] 参照上述引文,在这次军事行动中,光武帝派遣马援率领骑兵三千人,从五阮关出塞,主要是为了袭击乌桓。因为乌桓族人侦察到汉军的动向,提前主动撤退,使马援没能达到作战目的,而等马援引兵撤退时,又尾随追击汉军,迫使马援连夜逃入塞内。经过这次作战,乌桓部族有所壮大,转而攻击匈奴,逼迫匈奴向北迁徙,以致漠南人去地空。 三 随着北部边疆形势的转变,鉴于马援征讨乌桓的失败,加上乌桓与匈奴的争斗,光武帝对乌桓的治理方略,也做出了适应性的调整。 (建武)二十二年,匈奴国乱,乌桓乘弱击破之,匈奴转北徙数千里,漠南地空,帝乃以币帛赂乌桓。[18] 显然,乌桓之所以能击破匈奴,主要得益于匈奴的内乱。匈奴族人的北迁和漠南地区的空虚,引起了光武帝的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tusizia.com/tszcf/10867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背诵版临床实用方剂7言诀
- 下一篇文章: 没有了